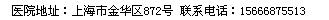您的当前位置:枕神经痛 > 影响危害 > 试析促织中营造的传奇优秀作文精选
试析促织中营造的传奇优秀作文精选
试析《促织》中营造的传奇原创作者
姚磊(江苏省宿迁市青华中学)“斗蟋蟀”,即蟋蟀相斗,是一项古老的民间搏戏活动,相传始于唐朝。《清稗类钞》云:“斗蟋蟀之戏,七月有之。始于唐天宝时,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而蓄之,以万金之资,付之一喙。”《开元天宝遗事》有“金笼蟋蟀”条,云“每至秋时,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,闭于笼中,置之枕函畔,夜听其声。庶民之家亦皆效之”。一、设计开头,埋下伏笔《促织》开头的亮点有两个:一个是:“此物故非西产”,第二个是:“有华阴令欲媚上官”。“此物故非西产”,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促织,为什么悲剧的故事会发生?鲁迅先生说,悲剧就是“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。”悲剧之所以会发生,因为无法回避。因为“宫中尚促织之戏”,又因为“岁征民间”,没有蟋蟀的地方发生了关于蟋蟀的悲剧,故事就有了荒诞的色彩,就有了魔幻的色彩。第二个亮点,“有华阴令欲媚上官”。“欲媚”是什么?“欲媚”其实就是奴性。封建文化根本就是奴性的文化。因为“欲媚”是递进的,所以,在《促织》里,悲剧就成了成名人生无法避免的法则。《促织》故事,一如苍山绵延,一如波涛汹涌。主人公成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作者用了四个字,“为人迂讷”。对比《促织》的另一个人物“里胥”。作者说,“里胥猾黠”。“迂讷”遇见了“猾黠”,两种性格的人,放在一起,冲突就发生了。性格决定命运。“滑黠”就是一阵狂风,卷住了一片“迂讷”的树叶,“滑黠”如同一盆凉水,浇的“迂讷”浑身尽湿,湿的透透的。作者写了成名的两次欲死,一次是“忧闷欲死”,一次是“惟思自尽”。如果说“忧闷欲死”是表示想死意向的话,那么“惟思自尽”就是表示唯死的决心了。成名因为交不起税负,又不肯勒索老百姓,所以“忧闷”。如果他和滑黠沆瀣一气,鱼肉乡里,也许就不会“忧闷”了。但是,成名毕竟是成名,不是“滑黠”,他有自己的性格发展逻辑。后来因为在规定时间内,交的蟋蟀不合格,被打的皮开肉绽,痛苦万分,于是想到了“自尽”。故事到这里,似乎到了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,但是,在古典小说和古代民间文学中,最大特点就是峰回路转。比如,时常会有这样的情节,午时三刻,法场上,刽子手正在举刀准备行刑,忽然就有马蹄声声,马上人振臂高呼,刀下留人。那种紧张的情绪,绷紧的神经,一下得到缓解,终于让人松了一口气,好人还是会有好报的。成名走到了绝路,没钱交付,又捉不到优质的蟋蟀,还能怎么办?唯有一死了之。二、曲径通幽,蜿蜒波折天无绝人之路。故事向相反的方向进行了,希望出现了。在这一段,故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,驼背巫。蒲松龄采用了白描的手法,写驼背巫“唇吻翕辟,不知何词”。就是上下嘴唇一张一合,营造一种神秘氛围,造成一种神奇的感觉。像神一样,有威慑力。有声音,有动作,但是听不清到底说什么,正因为如此,才制造了一种肃穆、紧张、神秘的氛围,以至于在场的所有人,都屏气凝神,“各各悚立以听”,所有的人都惊悚地站在那里听。这是一个静的几乎让人不能呼吸的大场景,每个人都等待命运的安排,等待神的帮助。成名在驼背巫的帮助下,终于得到他满意的促织了。这是一只什么样的促织呢?“巨身修尾,青项金翅。”“巨身”,个头很大,不是一般的大,而是“巨大”,说明这不是一般的蟋蟀。“修尾”,说明这只蟋蟀不是简单的大,更不是胖,而是有很好的身形,尾巴是修长的,如果没有这修尾,那么这只蟋蟀肯定不入流了。“青项”,脖子是青色的,说明这只蟋蟀年纪不大,正值青壮年,如果颜色发灰或者发黑,那么肯定是年纪较大的。“金翅”,说明这只蟋蟀不仅身形巨大,而且色彩耀眼。金色,寓意这只蟋蟀的高贵,不一般。蟋蟀的出处,即生长环境对蟋蟀影响很大。成名捉住的这只蟋蟀生于嶙峋怪石下,藏在石洞中。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虫语》中介绍:“蟋蟀,于草中出者少力,于石隙竹根生者坚老善斗。”更加确定这不是一只寻常的蟋蟀。这只“巨身修尾,青项金翅”的不一般的蟋蟀,拨动了我们的想象力。成名一家,得之高兴,作为读者,我们也替他高兴。有了这只蟋蟀,成名就好交差了,不用“忧闷”了,也不用想不开了。文本开始,写捉不到蟋蟀是“抑”,写得到驼背巫的帮助,捉到蟋蟀,是“扬”。接下来的情节应该是怎样的呢?交给县官,完成任务,皆大欢喜?作者引领着读者,撩动读者的情绪。悲剧有悲剧的原则,所有的欢乐都是为悲伤所积聚的基础。成名的儿子,一个九岁的孩子,正是好奇心旺盛的年龄,他的好奇心驱使他,想去看看那只神奇的蟋蟀。故事走到了“抑”的阶段,走到了死胡同,人物走到了悬崖边缘。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,再次熄灭。儿子调皮,把促织弄死了。成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?不是悲伤,而是愤怒,恨不得把孩子打死。当他去找孩子的时候,带着怒气,“怒索儿”。他是怒气冲冲去找孩子的。但是,等他从井里头把孩子的尸体捞上来之后,只能是“化怒为悲”。骨肉分离,阴阳相隔,情绪突然转化,由怒到悲。那悲痛的情绪,深入骨髓。蟋蟀的死,儿子的投井,这都已经发生了,面对这一连串的的事件,成名和妻子,他们的表现是怎样的呢?从对儿子弄死蟋蟀的愤怒,到对儿子投井后的悲痛欲绝,再到夫妻二人面对这一切时,作者用了八个字:“夫妻向隅,茅舍无烟。”这里用的写法也是白描。夫妻两个,一人对着一个墙角,都在发呆。茅草屋里冰冷无烟,灶里根本就没有烟火。简陋的茅草屋,发呆的成名,还有他的妻子,冰冷的灶台……那场面,是绝望的,是无助的。让人欲哭无泪。悲剧的气氛一下子就营造出来了,宛若眼前,栩栩如生。写人,也是写景;是描写,也是叙事。人与物、情与景是高度合一,情景交融,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从阅读效果来看,这八个字很让人痛苦,甚至包括生理性的痛苦。那种希望的破灭,那种失子之痛,那种一无所有的境遇,不光是心理上的情感上的痛苦,还有切切实实的生理上的折磨与打击。三、一波三折,峰回路转《促织》的故事发展到这里,是一个更大的“抑”,似乎成名一家走投无路了,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。但是,作者的艺术手法高超就表现在这里。这里首先出现了小幅度的“扬”,这个“扬”是什么呢?就是成名九岁的儿子的“起死回生”。从故事的发展逻辑来看,孩子是不能死的,真的死了这故事就说不下去了,所以,孩子得活过来。但是,完全恢复原来的状态也不行,解决不了捉蟋蟀问题。于是,作者就设计了一个细节,就是孩子恢复意识了,但是没有完全恢复,只恢复了一半。活过来了,但是人傻了。孩子为什么会傻了呢,这主要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,即孩子要变成促织。孩子活过来了,成名夫妇心里欣慰了许多。既然孩子没事了,更重要的事情,又摆在眼前了。所谓重要的事情,有时是根据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,孩子出事了,当然孩子的事情是最重要的,现在孩子没大碍了,捉蟋蟀的事情又跃居首位。所以这是成名“亦不复以儿为念”的缘由。这句话很无情,但是恰恰印证了苛税的严酷。另一方面,如果成名一门心思都在儿子的身上,故事又怎么往下发展呢?成名满心愁虑的时候,时间从深夜走到了早晨。接下来作者写了成名的两次心情,都是有关喜悦的。第一次,是听到了门外促织的叫声,成名“喜而捕之”,第二次是促织跳到了成名的衣袖上,成名看了看这个小虫子,“视之,形若土狗,梅花翅,方首,长胫,意似良。喜而收之。”让我们来察看一下作者是怎么写那只促织的,他一口气写了促织的五个动作。为了凸现这只促织的神奇,作者做了连续的铺排。第一个动作,促织“一鸣辄跃去,行且速”;第二个动作,“超忽而跃。急趋之”;第三个动作,“折过墙隅,迷其所在”,躲起来了;第四个动作,则干脆跳到了墙上,“伏壁上”。顽皮,可爱,像是在写一个可爱的孩子。第五个动作,读者可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,“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”,看着成名不